Emily开始要我唱摇篮曲的时候,刚满三岁。
那时我们一家还算完整。Sarah会在晚餐后帮Emily洗澡、选一件柔软的睡衣,再由我负责讲故事和唱歌。Emily不太喜欢睡前故事,说那会让她“脑子乱乱的”。她喜欢歌,尤其是《你是我的阳光》。
我们的作息总是很规律。八点洗澡,八点半躺上床,然后我关灯坐在床边,用低沉又柔和的嗓音唱著那首老歌。Emily会把她的小手放在我膝盖上,闭著眼,像是确认我还在。
“爸爸再唱一次。”
第一次她这样说,是在我唱完第二遍之后。
“你不是快睡著了吗?”我笑著揉揉她的头。
“可是那一遍有一点点太快,”她睁开眼,语气认真,“可以再唱一次,慢一点吗?”
我当然照做了。那晚我唱了四遍,她才轻声说“够了”,然后转身把自己缩进被子里。
这并不是什么大事。孩子嘛,对于声音的安全感往往远超过我们想像。我当时甚至有点高兴——代表她信任我,觉得我唱的歌能驱散夜里的怪兽。
但Emily的“再一次”很快成为了一种习惯。
四遍变成五遍,五遍变成七遍。有几晚甚至超过十次,而我也没特别在意。毕竟每个孩子都会有一段黏人的时期。这是我告诉自己的理由。
直到有一晚,我唱到第十六遍时,嗓子已经有点干哑,Emily却还是轻声说:
“爸爸,再一次。”
我停顿了一下。
“你不累吗,Emily?”
她摇摇头,在微弱的夜灯下,那双眼睛亮得不太真实。
“还不行,还没到那个数字。”
“什么数字?”
“我不知道,可是……要再几次才行。”
我心里微微一缩,但还是照她的话又唱了一遍。然后是下一遍。然后——总共二十二遍。
她终于满意地睡著了。
那之后我买了一本小笔记本,每天在右上角记上日期,然后记录当晚唱了几遍。这不是因为我觉得重要,而是单纯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夸张了。
结果数字倒是真的越来越多:平均下来每晚十五到二十遍,有时甚至超过三十。
Sarah开始受不了了。
“Jack,你不能这样宠她,”她在一次周日早餐时低声说,试图让Emily听不见,“你都唱快一个小时了,嗓子都哑了。”
“她睡不著,我能怎么办?”
“这就是问题啊,她必须学会自己入睡。”Sarah放下刀叉,皱眉看著我,“这样下去对她不好,也对你不好。”
我点点头,口头上表示同意,但那晚我还是坐在床边唱了二十七遍。
那一晚,Emily第一次主动把头靠在我腿上,闭著眼轻声说:“你唱得很准,爸爸。他们一定很喜欢。”
“他们?”
“……没什么。”她转过头,埋进枕头里。
我没有多问。那时候的我,只觉得她是随口说的。
我逐渐养成了一种奇怪的习惯:在午餐时间躲在会议室里练唱歌。不是为了参加什么表演,也不是想成为更好的父亲。我只是……不想唱错。
Emily开始会纠正我:“副歌那里你拉得太长了”,“第三遍跟第七遍之间的停顿不一样”、“第十四遍那次有点跑调”……
她说这些话的语气并不尖锐,只是冷静而精准,就像老师在纠正学生的默写。她从来不发脾气、不威胁我、不哭闹。但那种沉静的关注,比任何愤怒都更让我不安。
她在听,她一直在听,每一个音符、每一个气口。这个三岁的小孩,像一台音准分析仪。
有几次我试图缩短流程。想像中,我只要态度坚决一点,Emily应该能理解。
有一晚我只唱了十遍。
她没有说话,只是坐起身,睁著眼睛看著我。那不是撒娇,也不是发脾气。她就那样盯著我,像是在等待什么自然发生。
那个眼神,我记得很清楚。
它让我想起我童年时期某个夏天,曾经在乡下老家的仓库里和表哥一起抓到一只受伤的麻雀。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盒子里,打算喂它水,照顾它几天。它躺在角落里,不动,也不叫,只是静静地盯著我。那种眼神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罪恶感。
Emily看著我的时候,就是那样的眼神——但她没有受伤,也没有痛苦。她只是……在等待。
我撑不住了。
第十一遍、第十二遍……直到她满意地点点头,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,小声说:“这样好多了。”
我退出她的房间时已经十一点,Sarah站在走廊尽头,双臂抱胸。
“你在干嘛,Jack?”她轻声问。
“我……她今天有点累。”
“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。”她的眼神不像是在质问,更像是在害怕,“我们是不是……该带她去看看医生?”
我没回答。那一晚我们之间没有再多说一句话。
第二天起,Sarah就不再参与晚上的哄睡流程了。她会在晚餐后早早躲进卧室,把门锁上,然后开著白噪音机。房子另一头仍然会传出我一遍又一遍低声哼唱的旋律。
我不怪她。她只是……比较早意识到这一切不太对劲。
而我还沉浸在一种近乎崇拜的愚忠中,坚信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——就像学走路前会先跌倒很多次一样。
我开始留意时间。唱第一遍的时间,Emily闭眼的时间,整个房间安静下来的时间。我甚至开始怀疑,Emily是否真的睡著。她总是在最后一遍之后就“立刻”停止说话、停止动作,如同某种仪式达成后自动关闭的机械。
有时我会故意不关灯,想看她是不是真的睡著。
但她总是在最后一遍之后,正确地转身、拉被子、闭眼,动作完美得像排练过几百次。我从未看见她睁眼偷看我,也从未听见她梦话。
直到某天早晨,我在她房间捡到一本她用蜡笔画的涂鸦本。
封面上写著“唱歌本”,旁边画了一排歪歪扭扭的小人。他们站得很整齐,每个人嘴巴都张开著,像是在唱歌。背后是一堵灰色的墙,墙上有小小的洞,像是眼睛。
我翻开第一页,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字。一页一页往后翻,数字越来越密集,每个数字旁边都有一个记号,有些是星星,有些是圈,有些是像弯曲的符号,让我想起古老的谱号。
最末页写著一行字,弯弯曲曲,有点潦草,但我还是看懂了:
“唱错了他们会很生气,要唱对,唱完,才会安全。”
我合上那本涂鸦本,觉得背脊发凉。这不像是一般三岁小孩的涂鸦。里面没有太阳、没有动物、没有房子——只有数字、墙、人。
那一整天,我脑中反复想著那行话:“唱完,才会安全。”
那天晚上我唱了三十四遍,Emily露出了满足的微笑。然后她说:
“爸爸今天唱得比昨天准。他们说你快学会了。”
我强挤出一个笑容:“他们又是谁呢?”
她没有回答,只是转身躺好,像是突然失去了说话的兴趣。
我坐在床边多待了几分钟,望著墙上的夜灯微微闪烁。
那道墙与我们隔邻邻居的房子之间隔著一段空间——那是一间空著的储藏室,房仲说上一次出租是五年前,之后就再没人住。
我突然记得,某个晚上我曾在唱歌时听见一点声音。不是Emily的声音,而是另一个,轻轻的、模仿我的声音。
我当时以为是自己的回音。但现在想起来……那不像是我的声音,更像是某个小孩在墙的另一边,跟著我一起唱。
但也许我只是太累了。
我关灯,站起来,关上房门。那一晚,墙后什么声音也没有。
只有我的记忆,在唱第十九遍的副歌时,听见某处微不可闻地跟了一句:“…你从不会知道,亲爱的,我有多爱你……”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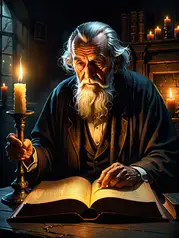
![]() 30
30
![]() 50
50
![]() 100
100
![]() 200
200
![]() 1000
1000
![]()
![]()
评论 0 则